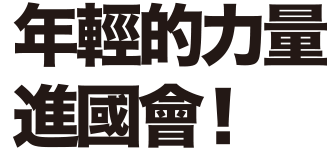青少年不是福利的依賴者,也不是需要保護的對象。青少年是權利的主體。
郝明義看到的這個人
見葉大華那天,因為一開始就發現了一位共同的朋友,所以我們的話匣子很容易就打開了。
訪問曾柏瑜、賈伯楷、洪慈庸等人,讓我對大學生年齡層的困境多了認識,和葉大華談,則讓我對高中生以下年齡層的問題,有了體會。
我說葉大華是「為青少年而起」,因為我相信讀者看過葉大華所講的,我們政府和社會給青少年製造的集體困境之後,也會同樣地拍案而起。
青少年包括了12歲至24歲的所有人。其中,葉大華那天主要談的,是她長期關注的18歲以下的青少年。
台灣15歲以上的青少年,工作就要繳稅;18歲以上,要負刑事完全責任,可是他們到20歲才有投票權的不合理,這我以前知道。
但是聽到葉大華接著說下面這些話,那種衝擊力隔了兩個月之後還是很強。
「只要你是學生,沒人當你是公民。」
「大人對青少年缺乏想像。唯一的想像是要他們趕快讀完書,然後趕快找到一份工作。」
葉大華講起話來表情豐富,很生動,連珠砲似地說這段話,簡直就是雄辯家了:「青少年不是福利的依賴者,也不是需要保護的對象。青少年是權利的主體。這就是世代正義。」
可是從訪問的過程中開始,到今天整理訪問稿,都一直有些問題盤旋在我腦中:
我們不都經過青少年嗎?每個人心裡不都有個青少年嗎?我們怎麼會始終如此堅持、始終毫不讓步地修理青少年呢?被修理的青少年長大之後又怎麼會繼續加入修理青少年的行列呢?
我實在不明白。
但起碼有一點值得高興的是,葉大華顯然不是這些人之一。
她在提醒我們:每個人都應該,也可以為青少年而起。
謝謝大華。
聽聽葉大華說的話

我大學一畢業,就投入在社會福利團體工作;後來工作一段時間去唸研究所,回來還是在社會福利團體工作。
二十年了,我專注於青少年的權益與福利政策,我跟我的團隊很努力的做政府該做卻沒做的事,但政府的主流教育還是停留在升學,十二年國教什麼超額比序、門檻之類的小圈子中打轉;大環境不好,永遠受害的是青少年,他們已經陷入了看不到未來的「集體困境」,非常嚴重。
我們台灣的青少年,24歲以下,共有600萬人,佔了全人口的1/3。其中18歲以下的有450萬人。
我曾經把有關18歲以下青少年福利預算都算上,政府每天花在每一位青少年身上的錢,最多也不到6元。
你說錢都用在教科文預算裏,但教科文預算也偏低,幾乎都用在養人,養專職人力、教師,投資在公益組織有限。我們的中途之家缺乏,青少年中途離校或輟學或家庭發生困難時,所能取得的資源太少。 這是非常弔詭的現象。
而18歲以下約有450萬的那些少年中,政府只關注兩頭,一頭是台灣之光,很有成就的那一群;另一頭是弱勢少年與虞犯少年,這一部分少年,大約佔了1/10,也就是45萬人。而對於弱勢少年與虞犯少年,除了安置、矯正、輔導,再也沒別的了。
但是另一方面,我們15歲以上的青少年,工作要繳稅;18歲以上,要負刑事完全責任,也就是負行為能力的責任。但憲法與民法卻又限定他們到了20歲,才享有權利,最明顯的就是投票權。
我們要矯正政府的就在這一點觀念:青少年不是福利的依賴者,也不是需要保護的對象。#青少年是權利的主體。
這就是世代正義。
把青少年該有的權力與權利還給他們,協助他們走出集體困境,在國高中時期就得培養他們生涯規劃和職涯發展的能力,而不是拖到大學。
我們不能老是把青少年當做 trouble maker。然後幫他們貼上了好手好腳的標籤,不像兒童一樣需要父母的支持、協助,可是卻又要把他們當成是身心不成熟的一群小屁孩。
他們的成長過程幾乎全丟給了教育體系,可是教育體系就那麼一點點的教科文預算,如何協助他們「轉大人」?
我們對青少年要有「轉大人」的概念。
他們遲早是社會的公民,政府得盡早投資他們具備社會參與的能力,培養他們公共意識的概念,經由審議民主的討論,讓他們有公民素養。 另外我們得注重他們的健康發展。這健康指的可不只是身體,而是成長環境,譬如媒體自律,保護他們的隱私,因為閱聽環境影響了他們社會化的過程。 當然,他們得有公平受教權。我們特別要關注的是這群遭逢了家庭經濟困境、家暴、性的侵害、未婚懷孕等問題而輟學的青少年,他們有甚麼需要協助的資源與支持體系?而不是只是被責罵與矯正,為了保護安置而中斷學業。
青年,不要認為他們沒有這些問題。 據教育部統計目前光是助學貸款,大專生一學期就有32萬人申請,其中私立大學申貸者是公立大學的四倍,社經背景愈佳的學生,進入公立學校機會更大,低社經背景學生進入公立學校機會較低。高教資源扭曲分配的結果,造成窮學生書越唸越窮,更難脫貧。
這就是青年困境最大的問題之一。
另一個大問題是資源分配,也就是前面所提的青少年的福利保障沒有公平機制,沒有投票權的人,更沒有權利參與資源分配。資源分配的不公,青少年是最大的受害者。
我們托育沒有真的公共化,就是給錢。但給了錢,也買不到服務,因為附近根本就沒有服務嘛;有,品質也不好,不是經常發生私立托兒所虐兒事件嗎?
政府對兒少、青少年的福利與教育政策,各項現金津貼比例不能佔太高,應該多投資培力青少年的發展、建全社會安全體系。目前現金津貼與投資發展的比例大概7:3,顛倒過來才是。
我們不能等青少年發生問題了才來補救,而是發生之前就該防止,在他掉下去之前,拉他一把,多點心理諮商師、輔導人員、等專業人員來幫忙,不能只光靠社工。也不能只光靠個案輔導,現在的個案輔導,不也是問題重重?
我們看反課綱運動,有很多長期考試受挫折的學生捲入,還有高職生。他們在這個運動中,找到了宣洩的出口。這是政府忽視與不作為的結果。 大人對青少年缺乏想像。唯一的想像是要他們趕快讀完書、盡快找到工作。
青少年有青少年的文化,這展現了他們在這個社會中的位置。例如塗鴨,大人老是認為這是搞破壞的次文化。但這早成了當代藝術的一環,是觀點與視野的問題。你要當作是藝術,還是搞破壞,其實只是個選擇。從反面來講,這是大人沒給青少年發展興趣的空間。
為了發展青少年創意塗鴨,我們多年前曾選中了西門町的電影主題公園,希望能規劃成青少年文創交流園區,並且加上職能培訓的平台。
但是,那時的台北市文化局長李永萍,說動都別想動,那塊只能做蚊子電影院,結果最後還不是虧了一堆錢。這就是政府嘛。
我進了國會要做的,和我會加入社民黨的原因是一樣的:我們都關心團結這個議題,社會團結,各階級的團結。所以我們也應該把青少年團結進這個社會,大家一起來參與改造這個社會,讓台灣能變得更好。
台灣很奇怪。青少年族群沒有公民身分、社會地位。
講個例子,你是學生,不管你是不是在社會做過事再回來讀書,或都已經是打工族了,只要你是學生,沒人當你是公民。 除非你脫離學生的身分,不然這個社會對你的限制很多。職場上也把你當菜鳥,低薪、被磨,還不能抗議,於是有了「慣老闆罵魯蛇」、「魯蛇批慣老闆」的流行話現象。 這是身分歧視,也是年齡歧視,更不要說18歲投票權的問題了。
權力義務完全不對等。這就造成了價值觀的衝突、階級衝突、世代衝突。
在選票利益的族群中,沒有人為青少年發聲,沒有人為他們喉舌。

今年(2015)本來有機會啟動修憲來進行公投降低投票年齡,但被國民黨硬綁住不在籍投票給推翻了,我們叫做「撕票」。
這件事給我很大的感觸,站在公民團體的立場,或者說,力量,我們能做該做的都做了,但這是政治,全世界只有我們和德國把投票年齡放在憲法中,但我們的修憲門檻又是全世界最高的,解決問題的設計卻反而讓問題給前制住了。
政府只想救失業率數字,沒想世代貧窮的問題,沒想解決這個問題,沒想團結各階層,讓青少年整合到體制中,進入社會運作。
進國會,我會盡全力推動有關青少年權益政策的法律,最重要的是訂定「青年發展法」。
台灣政府老是拿依法行政當藉口,那我們就立法,要求政府正向投資青年方案、計畫,讓青少年的學習教育、素養培力、民主意識、發聲平台、就業能力,都能得到充分的資源。
做為一個不分區的立委,要有代表全國的認知,代表弱勢、特定族群,便不可偏離公共議題。不分區立委,是全民的代理人,不能只聽黨意,要為全民發聲。
陳季芳的側記
葉大華非常年輕──語言年輕、動作年輕。
她說「魯蛇」,很順耳;她說「慣老闆」,我們摸不著頭腦,還請她解釋一下。她也沒放過順手拿手機拍照的機會,郝明義簽書,她拿起手機拍了好幾張,倒是我慢了好幾拍。
葉大華年輕,因為她從出社會就一直在年輕人的圈子裡工作。
她投入、感同,也身受,她為年輕人沒有出路的集體焦慮而焦慮,她為年輕人集體困境要打破困境,所以她成為綠社盟的不分區立委候選人。
她說,政府對年輕人投資太少,限制卻多得不得了。政府不肯承認兒少也是權利的主體,不肯承認街頭塗鴨也是藝術;而大學生一學期有32萬人揹著學貸,政府稍微關注了450萬青少年中弱勢的45萬人,而置其他400萬人於不顧。
她要把屬於青少年的權力要回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