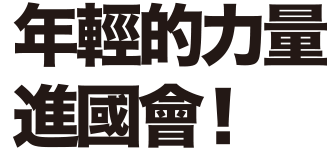土地的所有權屬於所有生物共有。人需要生活的空間,夠用就好,不能不斷地開發。
郝明義看到的這個人
武俠小說裡,會有這樣一個場面:一個隱名埋姓的人,從床下挪出一條滿是塵埃的長布包。他慢慢打開捲布,露出其中的長匣;打開長匣,其中一柄烏黑劍鞘;抽出長劍,鋒利耀目。
我見呂東杰,和他一路談話的感受,大致就像在經歷那個場面。
人不可貌相。呂東杰是一個隱俠。
那天去桃園見他的時候折騰了一陣,因為他沒有競選服務處,約在外頭一些地方我的輪椅進出又不便,好不容易在一家簡餐店見了面。
初見很不好說這是個什麼樣的人。從他那一頭不少白髮開始,就看來年輕不年輕,但說老也不多老;工作不像是上班族,但是務農還是做工,也說不準;說競選,到底是像立委參選人,還是像立委參選人的志工,也皆可。
他讀黎明技術學院畢業,曾經在統一超商工作了十二年,從大夜班的工作,做到行銷經理,負責引進Duskin。做Duskin的時候,呂東杰學習日本清潔文化,早晚讀《心經》。也因為做Duskin,他認識了一家德國清潔設備公司,後來決定出來創業,經營一家主要代理德國洗掃地機和清潔劑的公司(普羅科琳)。
經營了六年之後,因為這段時間從德國公司那裡又學習到環保的概念,對大自然有了敬畏之心,一路加入了荒野保護協會,認識其他生命的價值,也體會到要尊重每種生命在大自然裡都有其居住權。
這樣,到六年前,呂東杰決定放棄「利益思維」,親身實踐自己的信念。 呂東杰本來可以把公司全部資產賣掉變現,那也可以有幾千萬元。
「可是我看公司的員工有三十多人。有些人都中年了,怎麼再找其他工作?」呂東杰說。「所以,我就把公司股份全部送給了員工,讓他們自己經營。」而他自己,則空手離開,開始去實踐他所相信的「自然農法」。
呂東杰說他從沒買過一棟房子。因為他相信土地不該為人所擁有,而應該是所有的生物所共有。但是他卻能因為受到退休老農的信任,接受委託,在兩塊各一甲的土地上實踐自然農法。
呂東杰說他尤其會種樹。所以台東那塊土地原來是柚子園,經過他的手五年後,現在成了一片森林。「可是我也發現,一個人的時間有限,不能光靠我一個人。」呂東杰說。於是他開始教育工作,教其他的農民也用他的方法耕作。
可是他又發現這樣也太慢。政府為了搞開發,徵收土地的速度太快。美麗灣、大埔、航空城案,都給了他衝擊。他之前就和綠黨有來往,到三年前就決定加入綠黨,從參加政治選舉開始,準備進入體制,從根本上解決問題。
2014年呂東杰就想競選桃園市長,但是因為保證金的門檻而沒能成。「政治參與本來應該是每個人的權利,但是在台灣卻成了權貴的遊戲。」他說。
這也更加強了呂東杰這次參選立委的決心,並且更決心打一場不一樣的選戰的決心。他也和其他許多人一樣,親自做街頭說明、拜訪鄉里之外,但是他不辦募款餐會。

「我在百吉步道做生態解說,在公園裡做環境教育,使用我的專業知識,帶著逛公園的人了解園內生態,譬如埤塘。」呂東杰說,「我想借由這種公園教育,來幫助大家有些基本的生態。」
呂東杰的公園生態講解導遊,可以說就是他的募款活動。你捐點錢可以聽他講,不捐也可以聽他講。
他的對手是國民黨的孫大千。但他根本沒談孫大千什麼。
當隱俠扶劍而起,雖千萬人吾往矣的時候,對面多一個少一個人,不是他所顧慮的。
聽聽呂東杰說的話
我為什麼一次又一次的參選?
因為我們很認真的保護台灣土地,做死做活,也趕不上政府開發破壞的速度。這不從觀念改變,是不行的。
2014 年我要參選桃園市長,明明知道選不上,還是參選,因為不踏出這第一步,我們的想法其他人就不會知道。
我們想把競選當做公民發聲平台,我們的政見和其他候選人有對等的能見度;這些政見,不見得要我親自去實施,只要當選的人願意把好的政見拿去用,我們的目的就達成了。
我覺得每次選舉,全是買票,什麼養老津貼多少戶、婦幼津貼多少,很可笑,這種做法並不是為台灣與人民著想。
結果,我湊不到 200 萬競選保證金,只好棄選。
這也是很好笑的事。政治本來應該全民參與,#政治在台灣卻變成了權貴遊戲,用錢擋你。選市長 200 萬,選立委 20 萬,行政官比民意代表貴,繳了入場券,才能競選。然後,繼續比錢多,看板、宣傳車、插旗、文宣,還有贈品,如面紙、原子筆,或者大家吃個炒米粉、貢丸湯。這樣錢撒下來,光是在桃園選議員,就得花 3000 萬。
立委的選區比議員大兩倍,錢也得花兩倍。
這造成了錢越多,越容易當選。不說別的,光是看板,越多越有能見度,光靠看板就可以選上。但民眾根本沒接觸到候選人,這人做了什麼,有什麼政見,不重要了。
民主先進國家不是這樣的,譬如德國,入場券的金額,大概只要台幣兩萬多。
美國,各個候選人不准插旗,文宣是張貼在各地方政府辦公地點,鄰里密集公辦政見會;在公園共同舉辦造勢活動,很公平,也就是選舉公共化,有錢並不重要,重要的是政策。
台灣的選舉文化太特別了,拼命花一次性的錢,當選後賺回來。
台灣選舉很艱困。但我還是要出來選,走進政黨、走進體制,才有希望改革、改變。
我選擇綠黨和我觀念改變非常有關係。我的工作是從7-11的門市大夜班,後來晉升到行銷經理,再後來到關係企業Duskin也是再從基層送貨員做起。 Duskin 企業文化日本原汁原味搬到台灣,每天早晚全體員工念心經,讓我逐漸認識了日本的清潔文化,重視永續。
這算是我環保意識的啟蒙,加入了荒野保護協會。我慢慢的體認到土地不是只屬於人,而是屬於所有生物。
我們必須很公平看待每一個不同的生命,人類不能為了自己,剝奪了其他生物的生命權利土地的所有權是屬於所有生物共有。譬如 30 坪土地,變成了水泥房子,其他生活就沒有生存空間了。
我這輩子沒買過房子,當然人需要生活的空間,但夠用就好,不能不斷地開發。土地拿來買賣,更是荒謬,非常不合理。也因為亂開發,所以才會有土石流之類的人為災害。

我在宜蘭和大溪,各有一甲土地,可這些土地也不是我所擁有的,是退休的老農委託我經營的。
宜蘭那塊是柚子園,我讓柚子樹自生自滅,生物自然生活,5 年來變成了森林,可見樹木生物有它自然的生存法則,人類不該去破壞。
大溪這塊地,我用輪耕的方式,只耕作一半的土地,另一半雜草叢生,讓小生物居住,土地也獲得滋養。這種稻種菜,自己釀醬油,也足夠生活。
我覺得我自己這樣做還不夠,到各鄉村去推廣自然農法,也有人響應;我到各公園做生態,就立個牌子,人在旁邊等,有人願意,我就為帶他們到處參觀解說樹木花草,現在為了選舉,我放我募款箱,捐不捐沒關係。
我也到中小學校、幼稚園,拜託校長讓我在寒暑假開課,免費為小朋友講解生態,他們也很歡迎。#我希望每個人從小就建立了生態與環保觀念。
但是,這樣做有用嗎?我一個人可以照顧兩甲地,一百個人不過兩百甲,政府隨便一個開發案,超過我們十倍,一個航空城3,000公頃,大概也就是3,000甲地,一輛推土車,就毀了我們多少人多少時間的心血。
我們像愚公移山式的保護土地,永遠趕不上政府開發的速度。如果國土規劃、環保、農業政策的法令齊全就好了,我也不必這麼辛苦。
這只能在體制內改革,不走進體制不競選不行。這次選舉,我很有希望,依據國民黨的民調,七月開始競選活動,半個月的時間,我的支持度由3.5%跳到了 12%。
雖然我沒看板,不插旗,沒宣傳車,沒有媒體關注。但我親自拜訪每一位選民;我也是用最環保的方式競選,在每一個街角,利用紅綠燈換檔約一分鐘的時間,對機車騎士宣傳政見。
進入國會之後,我們綠黨很小,成立黨團很難,如果能獲得他黨合作提出法案是最好,至少我能做到讓國會透明化,公布協商內容,多讓人民理解國會在做什麼,這樣才能讓國會正常。
這當然有破壞性,但非常時期非常作法。
台灣一定得要有永續的觀念。
陳季芳的側記
大溪,慈湖所在地,慈湖路上,並不是一個友善的地方,處處有障礙,不便於輪椅。我們和呂東杰約,先到,也一直在電話裡改地點。星巴克不行,麥當勞不行,最後勉強找到了一家清爽的披薩店,呂東杰才匆匆趕到,所以,我見到一個穿著短褲、藍白拖、灰髮、稀稀疏疏幾絲鬍子的立委候選人。
只掠過一秒驚訝,立時遭到荒謬全面攻擊──荒謬的我站在荒謬的街道、荒謬的社會、荒謬的政治。
呂東杰是一個翻轉的人物。在都市體制中蒼老──小七的店長,又回歸於土地──自耕自足,對生態有無限的想像。
「土地所有權的概念,是生物共有,不是人類獨有。」
「但是,我們對土地的保護,永遠趕不上政府的開發。」
他很無力,他要選舉──用競選發聲。
我看著呂東杰,一片蒼茫的大地與孤獨的身影:枯藤老樹昏鴉,古道西風瘦馬。